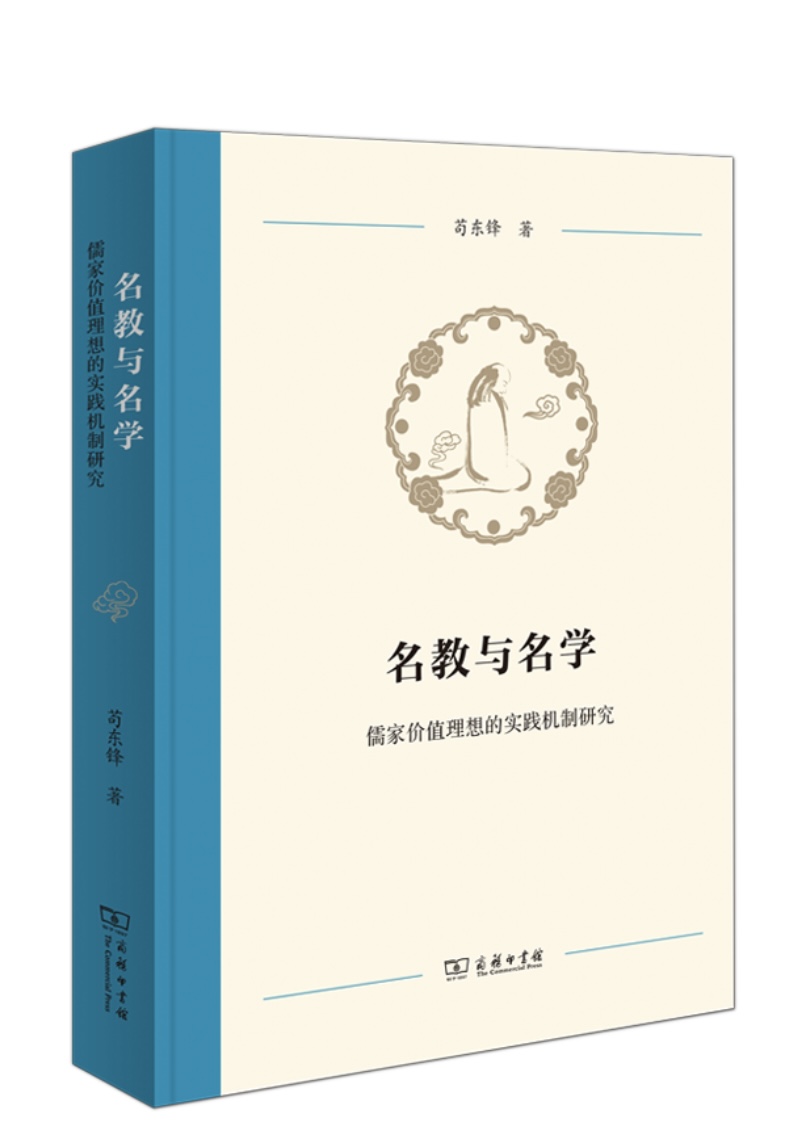
《名教与名学:儒家价值理想的实践机制研究》
作者:苟东锋
商务印书馆,2023年9月
内容简介
每个成熟的社会都需要一套核心价值观以维持其稳定和健康运行,名教即古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本书立定“新名学”立场,认为由孔子实质创立的儒家名学在先秦以后进展为以名教为形式的实践形态,其基本任务是设法使人产生践行儒家价值理想的道德动力。因为动力机制不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汉与宋明两种名教模型,它们各有特长与局限,由此主导了先秦以后儒家发展的起承转合。
名教自诞生起就一直面临各种挑战和机遇。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中国社会正在遭遇历史上第五次名教危机。名教未来是否退场取决于儒家价值理想的实践机制是否可由君子为平民操心的旧格局转变为公民为自身操心的新格局。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重建应当建基于名教的底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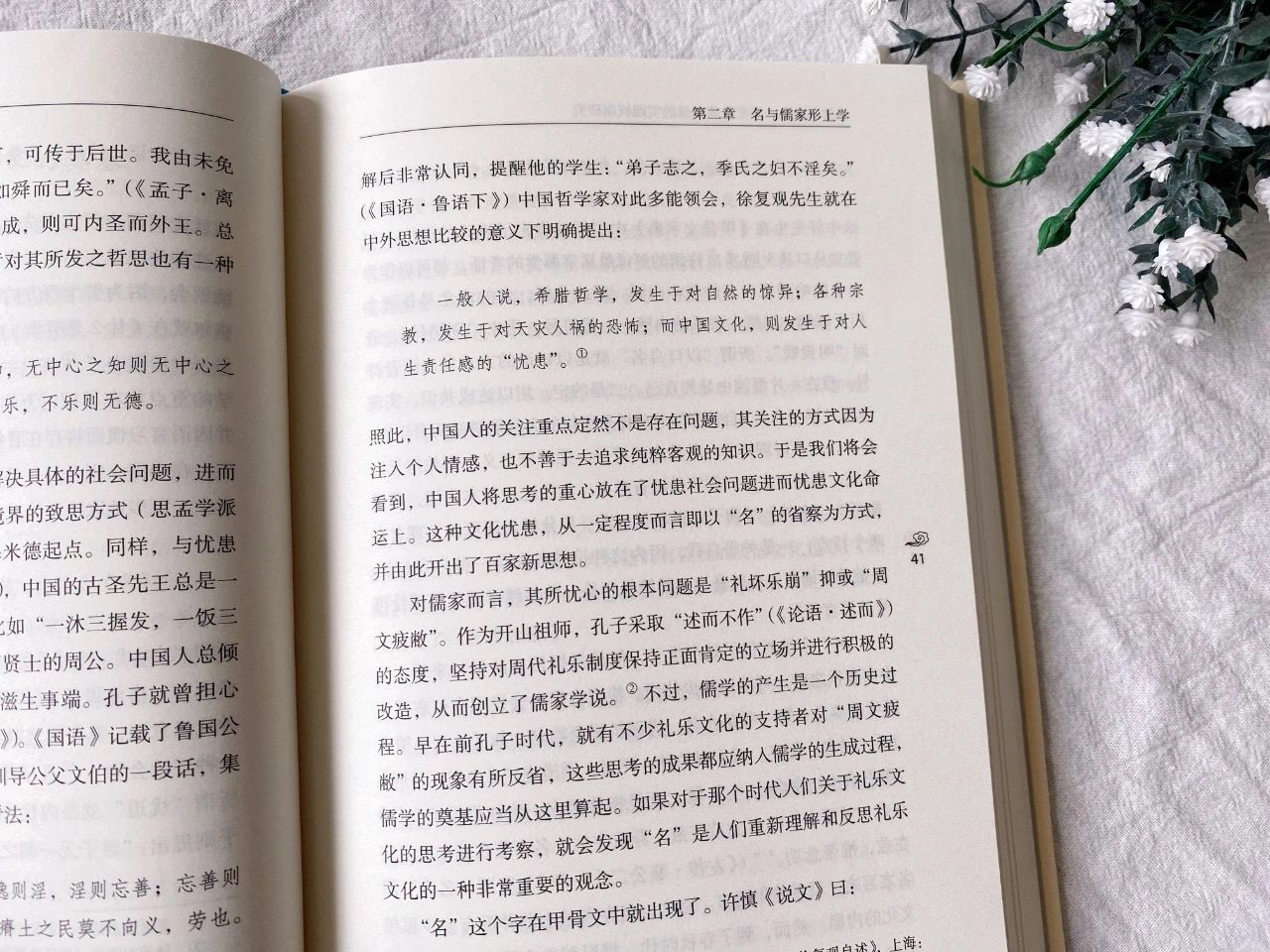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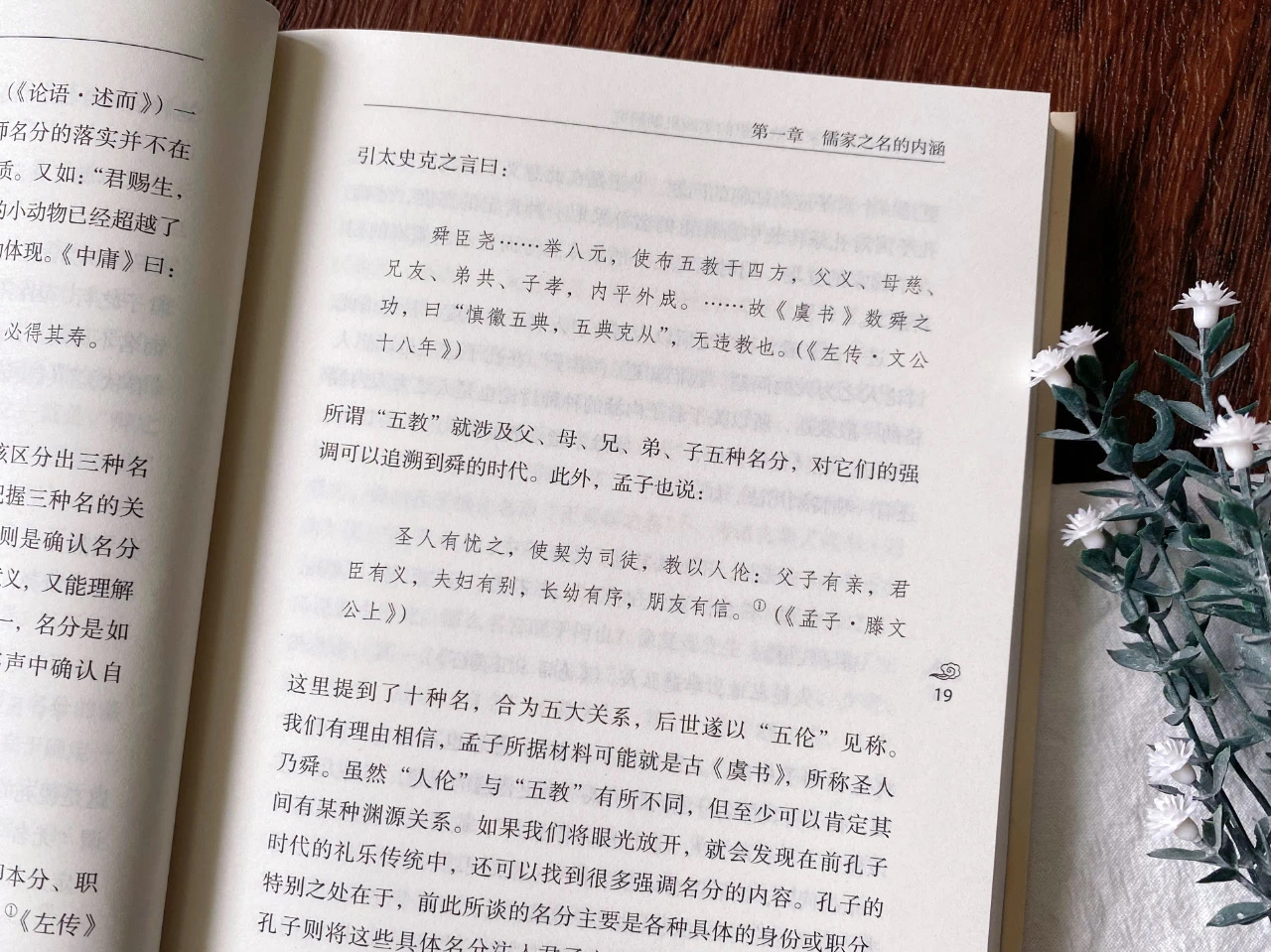
我为什么对“名教”的问题感兴趣?如今回想起来,脑海中首先跳出这样一段童年记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渭河平原一个普通乡村的老宅中,父亲接待了他的一位友人,二人正在闲聊。那段时间,我突然对大人们的聊天内容感到好奇,就凑过去听。只听父亲对友人讲:“那个某某,他现在不图利,而是图名呢!”
我之所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是因为他们的评论对象属于本地先富起来的那批成功人士。那人为去世的母亲举行三年之礼,大操大办,还大手笔地请来了省城的秦腔剧团,一时轰动乡里。这件不大不小的新闻自然引起乡邻的议论,大多数人都在一片赞叹中口称此人不愧为一个大大的孝子;也有一些人语带微讽地强调,与其在去世之后搞得这么轰轰烈烈,还不如生前就好好尽孝。当然,父亲与其友人的评论也是这些纷纷议论中的一种声音。我那时窃听了大人的聊天,心中不免产生了对成人世界的最初印象,那是一个“图名”的世界。
后来,我考上了一所南方的大学,即将远行。母亲不放心我一个人生活在那个遥远的异方,就要将毕生总结的处世之道传授给我。其中一点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她说:“你要学会夸赞别人,人人都爱听好话。”当然,她又补充道:“这可不是叫你毫无事实依据地谄媚别人。”母亲所讲的人生道理,刚开始我是不以为然的,然而渐渐发现,它确实充满智慧。
进而等我读到《论语》,赫然看到,她讲的话原来孔子早讲过了,只不过换成了古语。孔子说:“乐道人之善。”(《论语·季氏》)同时又讲:“恶称人之恶者。”(《论语·阳货》)还解释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紧接着,我在儒家典籍中印证了更多的观念和话语,它们显然都来自我的父母和故乡。
这种奇妙的体会令我对儒学顿生亲切之感,并最终选择了中国哲学作为研究生的专业,但也留下一个疑问:他们赋予我的这些价值观念来自哪里?
这个问题在脑中盘桓不去,使我不得不认真回眸我所出生的那块土地。作为周秦汉唐故地,关中文脉兴盛。王阳明曾经感叹:“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1]北宋时期,张载创立关学,后来成为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以及朱熹的闽学齐名的宋代理学四大流派之一,史称“濂洛关闽”。
宋元以后,关中理学一直保持兴盛态势,理学人才辈出,从明代的吕柟、冯从吾,一直到清初的李二曲,清末的刘古愚、牛兆濂,绵延传承。关学重践履和教化,张载的弟子吕大临、吕大均等制定了《蓝田吕氏乡约》,敦化风俗、劝民为善,开创了以儒学治理乡村的先河。这种儒学实践活动受到理学家的推崇,朱熹的《朱子增损吕氏乡约》,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以及近代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运动等均受其影响。
李泽厚指出:“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文化、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儒学孔学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学说、理论、思想,而是融化浸透在人们生活和心理之中了,成了这一民族心理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广大农民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孔子,但孔子开创的那一套由长期的宗法制度,从长幼尊卑的秩序到‘天地君师亲’的牌位,早已浸透在他们遵循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观念意识、思想感情。”[2]于是我就明白,原来我的父母、祖辈及乡邻自带的那种儒家观念来自由他们世代延续的生活方式所积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套观念近代以来虽经摧残,却依旧活在民间。
这种情况让我想起我们关中的一位名人乡党陈忠实和他的那部震动了现代文学史的作品《白鹿原》。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传统文化受到激烈批判,儒家的纲常名教成了罪恶的代名词。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3]自此以后,“仁义道德”就象征着“吃人”。
近代以来的文学作品无不将描写重点放在敢于批判传统的“新人物”上,《白鹿原》几乎是第一部从正面刻画“旧人物”的作品,进而庄重又艰难地重新书写出“仁义”二字。所以评论家雷达说:“《白鹿原》的思想意蕴要用最简括的话来说,就是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4]陈忠实之所以能突破“仁义吃人”的范式主要在于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从现实主义出发,任何一个有过关中基层生存经验的人,倘若躲过了流行观念的冲刷,又善于体察生活,都会承认传统观念并未远去。经历了近代以来一遍遍的革故鼎新运动,仁义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传统观念凭借着礼俗、人格、语言、曲艺、物件等方式依然屹立于人们的头脑中,诚如评论家孙豹隐所言:“白鹿原上,最坚实的基础不是别的,而是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存留下来的那一套伦理规范,几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那一种文化心理,几千年相沿流传的那一番乡俗风情。”[5]可以说,传统的价值观念至今发挥着某种积极作用。
当然,在这场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传统价值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显出僵化、迟钝以至迂腐的气息。在《白鹿原》中,仁义的正面价值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彰显,但是作者也客观冷静地呈现了仁义的消极面向。
比如作为“仁义白鹿村”之“仁义”象征的主人公白嘉轩,陈忠实就如是评价道:“白嘉轩身上负载了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精神,也负载了封建文明的全部糟粕和必须打破、消失的东西。否则这个民族就会毁灭。这些东西部分集中在他身上有时就变成非常残忍的一面,吃人的一面。”[6]
文学的现实价值在于以一种感性的方式发现和揭露问题,引人入胜,并在使人震撼之余触发人们的思考。至于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则有赖于学术研究。[7]当传统价值成为一个学术问题,我们的视野也会随之打开。
首先,传统价值应有简明切要的界定。我们认为,传统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就其根本而言可以统摄为名教问题。名教孕育于礼乐文化而由孔子正名思想所彰显。在孔子看来,人道世界由名分构成,每一个体都处于各种叠加名分中而形成人伦关系,所有名分都可以收摄于君子之名。进而言之,名必有义,义必可言,言必可行,行出于己,名(闻)定于人,构成了一种循环交织的价值实践系统。
照此思路,名教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价值理想的层面,仁义是其魂魄;另一个是实践机制层面,依仁由义是其指向。与此相关,名教有广狭二义:广义而言,凡以仁义为鹄的而定位自身的都属名教,汉唐儒与宋明儒都不离名教范围,其不同仅在价值理想的实践机制。狭义来讲,名教则特指汉代开创的“以名策善”[8]之术,其中的“名”是强调名声、名节和功名,“善”则指向作为名分之义的仁义之实,所谓“劝其立名,则获其实”。[9]从这个意义来讲,绵延至今的传统价值观主要是以名教方式存在。对此,我们既可以在认同传统价值信念的层面理解,又可以从价值理想的实践机制层面审视。
其次,须知名教自诞生起就一直遭遇着各种挑战。先秦时代,在儒家举起仁义大旗的同时,诸子的反对声音就不绝于耳。道家主张“大道废,有仁义”(《道德经·第十八章》),甚至提出“绝仁弃义,民复孝慈”(《道德经·第十九章》)。墨家则针对儒家指出:“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贵义》)。法家更以“仁义”为“六虱”之一(《商君书·靳令》),提倡“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汉书·艺文志》)。
魏晋时代,名教式微,玄学家发出“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的质疑,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10]。佛教传入中国,尽管声称与名教宗旨相通,所谓“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11]。然而,其判教立场依然十分明确:“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12]清代以后,理学衰落,戴震等学者则痛斥宋儒:“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13]
由此可见,“五四”以后我们正遭遇历史上第五次名教危机。严格来讲,此次危机所涉及的主要是宋明以后经过了统治阶层改造的一套名教实践机制。从价值理想层面而言,名教依然保持着顽强生命力,所需配套的只是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实践机制。
再次,应当肯定现代及未来中国仍需名教。作为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名教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年间大致起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具有统一性,这是政治的基本特点决定的,如果一个共同体中的成员感受不到某种统一的价值信念以供其断定是非对错,这个共同体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墨子很早就指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乱,若禽兽焉。”(《墨子·尚同》)儒家在这方面与墨家并无二致,并主张那个唯一的至高原则“义”只能是仁义。《孟子》一书开篇即言:“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言下之意,“在一个国家或一个伦理共同体内部,其所奉行的最高原则,必须是‘仁义’而绝不能是‘利’。”[14]
问题在于近代以来当中国处于一种新的国际局势中,应当标举怎样的一种核心价值观,才能一方面彰显国族存在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又能适应时代发展并在国际意识形态冲突中通达某种共生之域?无论如何,由孔夫子开创的名教传统都应成为当代核心价值建构的底色。
以上三点大致勾描了本书撰写的旨趣。就具体的写作内容来讲,本书一共设为三篇。
第一篇为内涵篇,主要在“新名学”的视域中界定了名教的基本含义,涉及儒家之名的三重内涵、儒家思想中的“名学三问”、名声观念以及始于汉代的狭义名教,最后对名教的模型及其内在理路进行了一种思想史的梳理,由此探索了名教的理论危机及其原因。
第二篇为理论篇,集中讨论了作为名教之源的孔子名学,由《论语》正名章及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孔子对名的问题的思考呈现为由五个环节构成的一种理论结构,分别涉及名论、义论、言论、行论、闻论,深入这些环节的内部以展开其中的问题并建构其间的关联是此篇的重点。
第三篇为实践篇,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从儒家发生学角度论述了“正名”这一立场所包含的礼的实践精神;二是从治生问题介入作为名教实践主体的士君子的古今之变;三是引入了正义和权利的话题,由此对传统名教的实践机制进行了深入反思,所得的结论是传统名教中君子为平民操心的格局必将转化为公民为自身操心的格局,此中呈现的趋势是权利观念由隐没而浮现。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名教问题有其复杂性的一面。近代以来,谭嗣同、章太炎、鲁迅、胡适、冯友兰等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名教批判思潮,至今依然没有停止甚至上升到对所谓“现代名教”的继续批判。[15]在此背景下,本书立足于当代儒学复兴的新形势提出名教尚未退场,应当且可以进行某种现代转化,这并不是做翻案文章,而是从理论上追本溯源,对名教观念的一种正名。名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然始终应当置于批判的视域进行审查[16],同时也应论衡其价值并审视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此之谓正名。至于这项正名工作做得如何,则有俟方家!
苟东锋
2022年11月11日